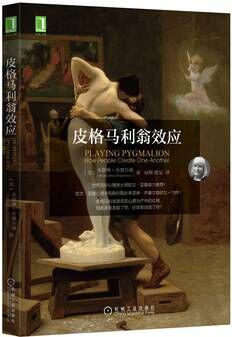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典故取自希腊神话,一位名叫皮格马利翁的雕刻家,爱上了自己的女神雕像,结果雕像真的变成了女神。这一效应用来指代由于心理预期的好或坏,导致结果真的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是自我预言的实现的延伸。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典故取自希腊神话,一位名叫皮格马利翁的雕刻家,爱上了自己的女神雕像,结果雕像真的变成了女神。这一效应用来指代由于心理预期的好或坏,导致结果真的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是自我预言的实现的延伸。
这本书探讨的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一个方面,即——我们在无意识中,对他人以及自身在他人世界中角色的设定,导致了我们行为和认知沿着这一设定发展。
我们就同皮格马利翁一样,在神话中爱上了自己的象牙雕像加拉泰亚(Galatea),女神维纳斯其后赐予了雕像生命。我们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欲望雕刻他人。然而,与皮格马利翁不同的是,我们也被他人雕刻——我们的加拉泰亚也有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有自己的主观性,即便我们希望不是这样。
当这些过程发生的时候,一个人在这场戏剧中既是导演又是主演。另一人成为我们的舞台上无意识的演员,我们对其巧妙、无意识地给出舞台指导(作为报偿,我们以某种方式演出对方的戏剧)。有的时候,这些无意识的、关键的舞台指导可能与我们说的话矛盾。
爱你,还是爱自己?
“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是对本书观点非常鲜明简洁的解读。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新属性,或是表现为一句新的口头禅、一种新的癖好,或是索性觉得自己彻底变了一个人。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由于尝试了新事物而发现自己潜在的一些特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需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一个需要表现自己勇敢的人小 A,可能会将周围的某个朋友小 B 设定为软弱的人,在一次次潜移默化的强化之后,这位朋友很可能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怂包。
先别为小 B 感到可怜……如果小 A 是小 B 的男友,或许这一现象就会被小 A 解读为找到了一个值得守护的人,而被小 B 解读为找到了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样的话,不也挺棒的吗?
等等……这似乎隐隐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妥,不是说好“爱一个人就爱他的全部,不要改变他”吗?
矮油,不要这么政治正确嘛!而且,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不改变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没有必要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都没什么改变,那社交的作用又何在呢?
我们在跟人的相互作用中创造自己,也创造彼此的关系。我们请人出演我们的剧目,对方也请我们饰演他们的剧中人。我们很少仔细地审视自己在别人生活中的角色,只要对方在我们的剧中表现令人满意。
我们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都是独特的:跟这一个,我们更乐意说些俏皮话;跟那一个,我们会高谈阔论,用上最高超的演说技巧。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分享的话题兴趣不同,更是因为,在不同的交往中,我们自己的不同方面与我们在对方身上细心挑出的特质相碰撞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各不相同。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和一个人相处舒服,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人,可能并不完全出于喜欢那个客观上存在的他,而是他满足了我们的剧本需要,或者我们喜欢自己在他剧本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喜欢的可能是那个幻想出来的他,或者,我们幻想的他们幻想中的我们。
然而,什么又是“客观上”的一个人呢?每个人在不同人那里的表现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使我们不得不怀疑,综合考虑后取的均值在多大程度上还有意义。
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因为“真实的自我”而被别人肯定。一方面,努力地把自己改造得迎合众人心意,而当这样的的自己被别人认可之后,欣慰的心情中又夹杂着许多的矛盾。这都是因为在意识中做了满足别人幻想的事,而如果是在无意识中做的(像在任何人际关系中你已经做了的那样),就会舒服得多。
所以,对于改变了别人和被别人改变这件事,其实并不用太在意。如果这是幻想,如果它让你舒服,继续做着梦就好,真实与否又有什么要紧,更何况“真实”在这个维度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更不要去执着自己爱的是一个真实的对方,或是对方爱的是否是幻想出的自己这种问题。如果此刻你的感觉是对的,那就是对的。
恨你,还是恨自己?
有趣的是,我们不仅会把别人幻想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还会让人难以置信地把别人幻想成我们讨厌害怕的样子,并且最终真的把他们变成那样子。
苛刻的、有迫害倾向的那部分自己,很可能由跟自己亲近的某人来代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与外部的事物斗争要比与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斗争来得容易。或者,我们在孩提时代想要逗笑的那位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似乎会在伴侣或亲密朋友身上继续存在,带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痛苦的安全感。
他们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把对方变成了自己最想要逃离的人。他们都无意识地看到了对方饰演自己最恐惧角色的隐藏的能力,然后,也是无意识地,开始把那种能力带进戏里。
我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想要把对方变成自己讨厌的那样,但是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只有在对方变成魔鬼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确信自己不是魔鬼?
不疯魔,不成佛。
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幻想而毁灭自己,会不会,也是一种很美的事?

